“韦伯之问”与人类文明互鉴
过去一二百年间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关于中国的诸多全局性“世界之问”。这些由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提出的“世界之问”展示了因中西文明传承、社会发展、文化体验与学术传统迥异而致的“他者”视角。其中,“韦伯之问”就是引发热议、影响深远的中国学核心议题之一。当下我们在文明互鉴视域下重估“韦伯之问”,对于超越西方先发现代性、构建新型人类现代性,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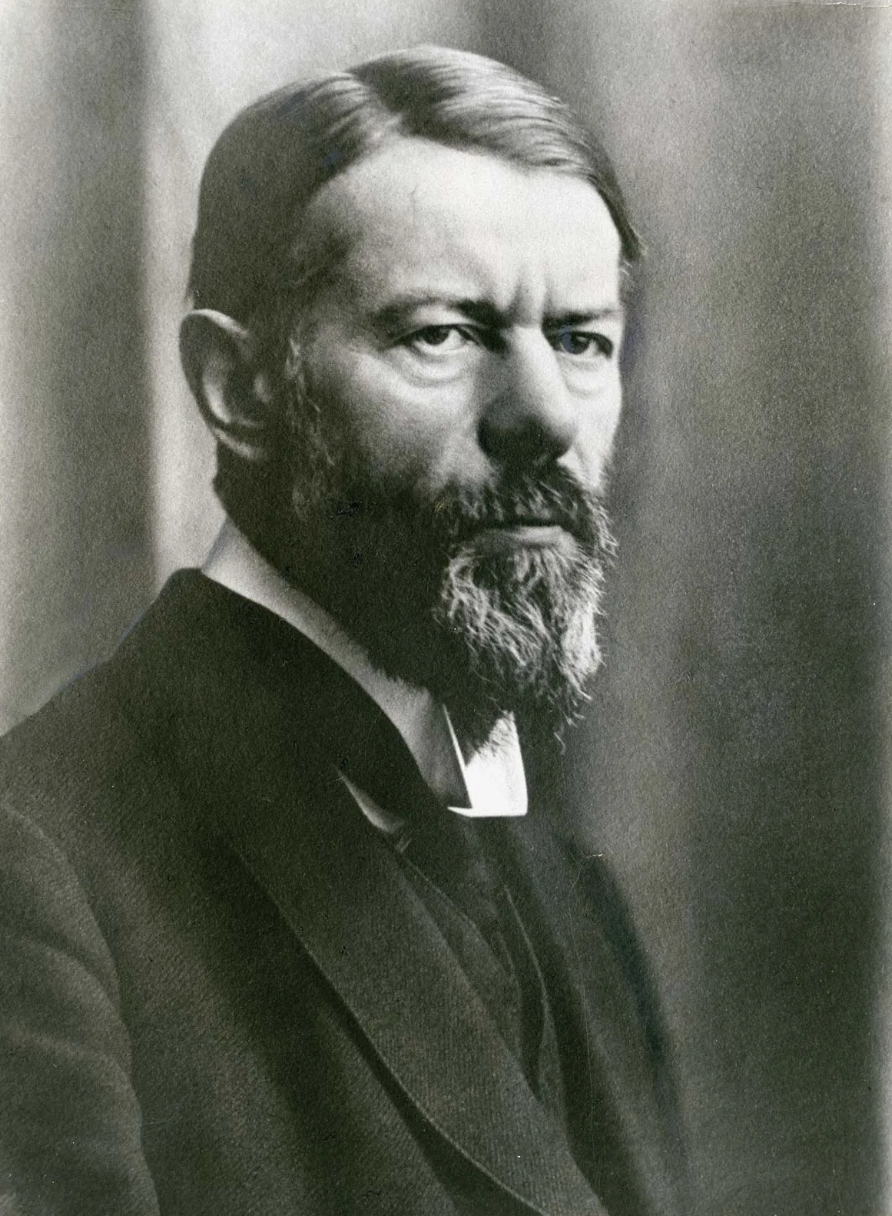
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现代性与中国研究
百余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基于其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研究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提出著名的“韦伯之问”,即:为何近代西欧能够发展出以理性化、世俗化、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而传统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等非西方文明却未能自发产生类似的资本主义?韦伯把基督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惊人大发展相联系,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为何的问题首先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货币量从何而来,而是尤其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之发展的问题。”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对比了中西宗教差异、探讨两者对塑造不同经济体系的作用,并将这种思想应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未领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解释,首先检视中国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与社会形式等有利或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诸要素;其次对比儒道思想与新教伦理,指出新教精神是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鼓舞力量,中国因缺乏该精神而无法发生资本主义;最后点明道家的保守思想无法发展出积极的奋斗动力、以发展资本主义。韦伯中国研究所使用的二手文献影响到他对历史分析的客观性,对中国切身体悟的缺乏促使韦伯开展中国研究时主要凭借天才想象和逻辑推理,因此致使韦伯对中国文明结构和儒道思想的阐述存在先天性不足。
韦伯将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缺失完全归因于文化价值,忽略了全球格局、政治、军事等复杂因素的多元交织性互动。这种视角单一的分析框架无疑不利于达成对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深广中国的认知。他把时间性的理性主义出现的西方社会条件问题,转变成空间性的精神文明领域的全球普遍适用问题,认为是中西宗教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东西“分流”的不同后果,从而凸显出西方近代文明之于非西方文明的“优异”特质。韦伯的中国研究思想其实也是西方近代文明逐渐统治世界的一个必然反映。
韦伯中国研究的理论建基于当时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发展观之上,隐含了一种将西方的理性化、先发资本主义视为人类文明“终极形态”的“西方中心论”叙事,其他文明因未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而被视为“落后”或“停滞”。这种视角在欧美学术界曾长期主导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甚至成为“文明优劣论”的理论依据。韦伯中国学范式因其问题意识、中国认知与研究方法在欧洲的典型性构成西方中国学的早期研究范式。
从人类文明互鉴视域重估韦伯理论遗产
除了阐述中国等非西方地区未能率先产生现代性的“宗教文明根因”外,韦伯还揭示了西方先发现代性的“牢笼”本质。韦伯发现,在工具理性极大推动西方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类个体的自由也愈益受到官僚规则约束、统治,工具理性扩张导致人陷入物化和工具化的存在,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以资本逻辑主导、工具理性独大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性通过殖民扩张导致自身内在缺陷的全球复制,诸如战争暴力、生态污染、精神匮乏等人类社会问题,可见存在先天缺陷的西方现代性并非人类现代性的最理想类型,这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因此,发掘并整合人类各文明资源,在价值领域结合各民族文明中的思想智识,有助于我们反思“工具理性”至上,构建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类现代性。
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多元异质文明对现代性有着不同层面的助益作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纠正西方先发现代性弊病的丰富价值理性内涵。例如,基督新教循道宗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对社会的关怀,伊斯兰教《古兰经》教义注重公平、友爱、宽容和凝聚力的伦理取向,强调公共责任和集体福祉。部分印度宗教和美洲宗教中亦含有敬畏自然万物、推崇社会和谐的因素,这与韦伯将禁欲主义与理性经济活动相联系的新教伦理不同,然而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助益经济增长、人心活力和社会进步同样重要。
历史实际发展进程表明,西欧的近代崛起和社会转型亦极大受益于对中世纪阿拉伯国家自然科学和中国社会制度因素的纳入。因此,辩证分析西方现代性、纳入非西方文明的优秀思想价值无疑为超越西方近代价值导向下的先发现代性,构建更健康、进步的人类现代性提供修正方案,从而破解“韦伯之问”。
从中国式现代化审视“韦伯之问”
韦伯之后世界史发展和半世纪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崛起促使世界重新思考文明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之间的丰富内涵,反映了韦伯中国研究的偏谬,及其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人类文明“终极形态”叙事的局限性。重估“韦伯之问”意味着对跨文明比较、传统与现代、多元现代性等问题的持续省思,世界中国学研究也在对“韦伯之问”的不断追问和时空转换中实现了推陈出新的发展。
一方面,人类不同文化的多元表述和共通内涵。韦伯阐述的禁欲、勤俭等新教伦理作为西方现代性发生动力的新教价值某种程度上是东西方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历史上弘扬“勤俭”精神的表述不可胜数,诸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故事,唐代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诗人李商隐曾作诗《咏史》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可见韦伯所言的新教精神在中华文明中亦可寻迹。东西文化除了殊异外,不同地区的百姓在心理结构上亦有共通之处。
另一方面,中西文明特质对于现代性的不同贡献和反思推进。儒家倡导奉献的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成就的思想动力,与韦伯强调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成功之关键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儒家思想中的公益心、同理心、信用、诚实、仁爱、团结等异于西方民主、自由的特质促使中国同样形成了为社会福祉、和谐稳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儒商文化”,而这迥异于新教伦理塑造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中国历史上济宁士绅对当地商业和“新生事物”的积极作为,就是韦伯强调儒家思想仅适应社会的反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亦修正了韦伯强调儒家思想适应社会、中国不能发展企业家精神的观点。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表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生态观,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启示,从而纠正了韦伯认为道家思想中的“神秘主义”“无为”之理念无法推动中国社会理性化发展的认知。
“韦伯之问”已提出百余年,东亚儒家文化圈和“全球南方”等的群体性崛起意味着,东西方的当代发展逐渐呈现与近现代东西方“大分流”不同的新图景。重估“韦伯之问”促使我们反思西方启蒙理性,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探索世界各地基于自身文明的多元现代化路径,进而在文明互鉴中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推动建立解答“古今中西之争”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新范式。








